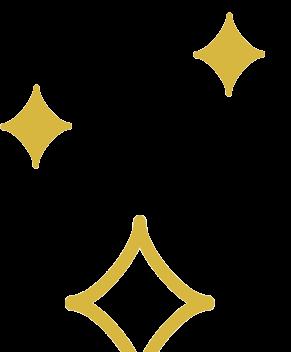
李贺诗歌的艺术成就无疑是全面的,但本文仅就其诗歌的奇妙构思、意象与用字的特点及通感等艺术特色作些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对其诗歌的艺术渊源进行考察,对其诗歌在后世产生的艺术影响进行简要论述。

△《李贺集》,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国古代文学史》(中)推荐阅读文献,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资助、岳麓书社2003年出版,王友胜、李德辉校注
一
李贺还喜欢运用跳跃的艺术结构,且看《长歌续短歌》:“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秦王不可见,旦夕成内热。渴饮壶中酒,饥拔陇头粟。凄凉四月阑,千里一时绿。夜峰何离离,明月落石底。徘徊沿石寻,照出高峰外。不得与之游,歌成鬓先改”前四句先言英主已逝,接下四句写青春不再,最后六句写明月难寻,彼此之间意绪跳跃性很大,忽儿天上,忽儿地下,忽儿白天,忽儿夜晚,忽儿往古,忽儿眼前,给人的感觉是片断的、不连贯的、不不完整的,虽有奇句,整首诗的脉络却难于把握。
造成李贺诗歌这一艺术特质的缘由在于:李贺写诗与他人不同,他人先得题而后为诗,李贺则每日骑驴背破锦囊,边行边吟,遇佳句即记下后投入囊中,晚上回家后再整理成诗。由于他在诗的章法、布局、命意上不甚着力,只是将不同时间、不同环境下所写的片言只句联缀成章,故诗歌有句无篇,在章法上难免有些散乱与疏漏,给人以零碎、拼凑的感觉,读者殊觉思维混乱,语无伦次。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历来对李贺诗歌的评价往往都离不开一个“奇”字,如张碧说他“奇峭”,张戒说他“瑰奇”,周紫芝说他“语奇而入怪”,晁公武说他“奇诡”,王应麟说他“奇僻”,屠隆说他“奇瑰”“耽奇”,谢榛说他“奇古”,沈德潜说他“瑰奇”,乔亿说他“奇涩”。杜牧为其诗集作序时,具体而形象地从九个方面阐明了李贺诗歌的艺术特点,尤其对其奇险特点的评价具有开宗明义的意义:“荒国
 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吸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李贺像
其次,李贺在诗歌创作时,因物感于心,善于捕捉丰富的意象,以此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李贺诗歌意象的基本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二就意象的分布而言,李贺诗中运用色彩意象最多,其敷彩设色的艺术也很独特。据学者统计,李贺诗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颜色是:“白”字83次,“红”字、“青”字各68次,“黄”字、“绿”字各43次,“粉”字、“碧”字各26次,“紫”字24次。此外,尚有“黑”字11次,“赤”字8次,“褐”字、“黛”字各两次。李贺对色彩如此敏感、酷爱,在诗歌中镶嵌如此繁多密集的色彩词藻,这在古代诗人中还是比较突出的。李贺刻意创造出层现叠出、浓重富艳的具有绮丽色彩的意象是为了在读者的眼前与心中唤起强烈的视觉感受,以此激发读者无比丰富的想像与联想,将其引入诗的意境中去。
三就其意象的性质而言,李贺诗歌意象具有柔婉与冷艳的特色。李贺选择的人文意象集中在女性的衣饰、体态、称呼,闺房内的装饰与用物,如服饰中有装饰女性的环、瑶、衫、袖、簪、裙等意象。使用这些质感上偏于阴冷的意象,以与诗人写作的小桥流水、荷塘月色、杏花春雨等景色相配。元好问评秦观诗“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实际上,李贺的创作也近于“女郎诗”。
再次,李贺诗用字、使词及造句,力避平淡浅易,不愿使用“经人道语”,力求“笔补造化”,创造了许多名言警句,形成了出俗反常、瑰美奇峭的语言特色。
受韩愈古文“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影响,李贺在使用语言上,尽量避俗求新而不拾人牙慧,明代李维桢《李贺诗解序》谓其“只字片语,必新必奇”,如《秋来》诗中“思牵今夜肠应直”,历来形容愁思多用“愁肠百结”,李贺则反其道而行之,谓纡曲的肠变直了。李贺在语言上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他自己,如写月就用了“宫蟾”“蟾光”“宝镜”“玉盘”“悬”“玉轮”“玉钩”“明弓”“斜白”等不同词语;写银河则用“天河”“天江”“银湾”“银浦”等不同词语。而在《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六月》诗中,同样是写太阳,将早晨初升的太阳比做“红镜”,上升运行的太阳比做“车轮”,中午的太阳比做“赤帝”(火神)。李贺尤其工于炼字,如“更容一夜抽千尺”,以“抽”字状竹笋生长之迅猛;“天河之水夜飞入”,以“飞”字形容银河之水陡涨;“长刀直立割鸣筝”,以“割”字描绘鸿门宴的紧张气氛;“一双瞳人剪秋水”,“剪”字活现出大眼睛扑闪的神态;“独携大胆出秦门”,“携”字勾画出吕将军勇武的神气。正因为如此,李贺诗中还出现了一些成语,如“笔补造化”“石破天惊”“天荒地老”“黑云压城”及“飞香走红”等,已为人们所流传。
在字的选择上,李贺喜欢用那些怪诞奇峭的字,王思任《李贺诗解序》说他“以哀激之思,作晦僻之调,喜用鬼字、泣字、死字、血字。幽冷
 刻,法当得夭。”李嘉言先生在《李贺与晚唐》一文中也说李贺“爱用惊人的字眼与句法,如腥、泻、惨、死、古、冷、孤、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指出了李贺用僻字的心理特征、情感意蕴与社会背景。
刻,法当得夭。”李嘉言先生在《李贺与晚唐》一文中也说李贺“爱用惊人的字眼与句法,如腥、泻、惨、死、古、冷、孤、仙、龙、蛇、鬼等,这分明是在极度的感伤中需要一些刺激来麻醉一时,也是他对于时代失望、疲倦之余的一种不正常的病象。”指出了李贺用僻字的心理特征、情感意蕴与社会背景。
李贺还长于运用色彩性强的字,诗中绿红交映、色彩缤纷,故陆游说“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
 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如《雁门太守行》一诗中则同时运用了“黑云”“甲光”“金鳞”“秋色”“燕脂”“夜紫”“红旗”“黄金”“玉龙”等一系列色彩斑斓的词汇,组成了一幅绚烂多姿的古战场画面,令人眼花缭乱。清代马位《秋窗随笔》也说“长吉善用‘白’字,如‘雄鸡一声天下白’‘吟诗一夜东方白’‘蓟门白于水’‘一夜绿房迎白晓’‘一山唯白晓’,皆奇句。”当然,李贺诗有时刻意雕琢涂饰,过于标新立异,将诗意掩盖于华丽的辞藻中,难免晦涩费解,失去了诗歌语言天真自然的另一种美,并由此遭到了后人的尖锐批评。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说“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也说“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
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如《雁门太守行》一诗中则同时运用了“黑云”“甲光”“金鳞”“秋色”“燕脂”“夜紫”“红旗”“黄金”“玉龙”等一系列色彩斑斓的词汇,组成了一幅绚烂多姿的古战场画面,令人眼花缭乱。清代马位《秋窗随笔》也说“长吉善用‘白’字,如‘雄鸡一声天下白’‘吟诗一夜东方白’‘蓟门白于水’‘一夜绿房迎白晓’‘一山唯白晓’,皆奇句。”当然,李贺诗有时刻意雕琢涂饰,过于标新立异,将诗意掩盖于华丽的辞藻中,难免晦涩费解,失去了诗歌语言天真自然的另一种美,并由此遭到了后人的尖锐批评。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卷一说“李长吉锦囊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明李东阳《麓堂诗话》也说“李长吉诗,字字句句欲传世,顾过于刿
 ,无天真自然之趣,有山节藻
,无天真自然之趣,有山节藻
 而无梁栋,知非大道也。”结合李贺部分过于奇险晦涩的诗句来看,这些批评还是较为恰当的。
而无梁栋,知非大道也。”结合李贺部分过于奇险晦涩的诗句来看,这些批评还是较为恰当的。
关于通感,古代批评家未曾涉及,《辞源》中没有此词,就是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也没有专门论述。钱钟书先生率先在《通感》一文讨论这一修辞手法,他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体质。”钱先生例举了李贺《恼公》“歌声春草露,门掩杏花丛”,《胡蝶飞》“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天上谣》“天河夜转漂回星,银浦流云学水声”等他分析第一例说“歌如珠,露如珠,两者都是套语陈言,李贺化腐为奇,来一下转移:‘歌如珠,露如珠,所以歌如露。’”这样就将看不见摸不着的“歌声”(听觉)转换成了具体形象的“草露”(视觉)。
李贺有天赋的感觉、知觉串连和表象联想的能力,这为他在诗中运用通感这一修辞手法创造了条件。在各种感觉的互通中,李贺运用得最多最成功的是视觉与听觉的互通。如《李凭箜篌引》“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玉为珍宝,一般不会让它破碎,凤凰乃神鸟,谁也没听见它鸣叫;至于芙蓉、香兰则更不会“泣”“笑”,显然是诗人在以视觉感受的美去体验箜篌的美妙乐声。在其他感觉的互通中,李贺也经常运用,风可以是酸风、香风、苦风,如“东关酸风射眸子”,“罗纬绣幕围香风”,“苦风吹朔寒”;雨可以是香雨、红雨、冷雨,如“依微香雨青氛氲”,“桃花乱落红如雨”“雨冷香魂吊书客”;雾可以是绿雾、暖雾,如“江中绿雾起凉波”,“暖雾驱云扑天地”。

△《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著,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
二
李贺诗歌艺术能取得炉火纯青的成就,形成独具一格的“长吉体”(或曰“昌谷体”),这决不是偶然的,除了他潜于诗艺、勤奋刻苦的写作态度外,还与他转益多师,合理地汲取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艺术营养不无关联。而且,他不是不加选择地汲取,而是通过自己的熔冶消化,深化提高,从而运用于诗歌创作的。
首先,李贺继承了屈原、李白等人的浪漫主义文学传统,其《赠陈商》自谓“楞伽堆案前,《楚辞》系肘后”,可见《楚辞》是他随身携带与阅读的。杜牧在《李贺集序》中早就指出李贺“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清代施补华《岘
 说诗》也说“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楚辞》来。”王琦则具体地指出李贺《帝子歌》“全仿《楚辞·九歌》”,方扶南又说“《神弦》三首,皆学《九歌·山鬼》”。李贺诗歌巧于比喻,用典灵活,用词下字工于着色,多用比兴象征手法与神话传说题材,这些的确与屈原创作的特点比较接近。即便是某些诗题也源于《楚辞》,如《浩歌》取自《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
说诗》也说“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楚辞》来。”王琦则具体地指出李贺《帝子歌》“全仿《楚辞·九歌》”,方扶南又说“《神弦》三首,皆学《九歌·山鬼》”。李贺诗歌巧于比喻,用典灵活,用词下字工于着色,多用比兴象征手法与神话传说题材,这些的确与屈原创作的特点比较接近。即便是某些诗题也源于《楚辞》,如《浩歌》取自《九歌·少司命》“望美人兮未来,临风
 兮浩歌。”至于李贺与李白的渊源关系,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也说“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又云“长吉险怪,虽儿语自得,然太白亦滥觞一二”。指出李白大量写乐府诗,多用幻语,诗风瑰奇,颇见波澜变化的特点对李贺产生影响。另外,李贺的游仙诗也多是从李白同类诗中引发来的。
兮浩歌。”至于李贺与李白的渊源关系,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说“贺诗乃李白乐府中出,瑰奇谲怪则似之,秀逸天拔则不及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也说“太白幻语,为长吉之滥觞”,又云“长吉险怪,虽儿语自得,然太白亦滥觞一二”。指出李白大量写乐府诗,多用幻语,诗风瑰奇,颇见波澜变化的特点对李贺产生影响。另外,李贺的游仙诗也多是从李白同类诗中引发来的。
其次,李贺诗歌创作也渊源于汉魏六朝乐府与齐梁宫体诗。其《花游曲序》曾夫子自道,“采梁简文诗调,赋《花游曲》,与妓弹唱”,而《雁门太守行》诗,王琦则曰:“梁简文帝之作,始言边城征战之思,长吉所拟,盖祖其意”。可见李贺的诗是汲取了梁简文帝同类作品的养分的。而《美人梳头歌》《残丝曲》《莫愁曲》等诗一望诗题即知是渊源于南朝宫体。对此前人曾有大量论述,同时人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诗序》说“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明代徐献忠《唐诗品》说“长吉陈诗藻缋,根本六代,而流调婉转,盖出于古乐府”;清人方扶南在批点李贺《将进酒》时,也称此诗“太似鲍照”;近代宋育仁《三唐诗品》说李贺“其源出于汉乐府歌谣,而拮藻于江淹、庾信。”朱自清先生在《李贺年谱》中对此论述尤详,他说“贺乐府歌诗盖上承梁代‘宫体’,下为温庭筠、李商隐、李群玉开路。”“唐人承六代遗习,极重乐府歌诗……则贺之以乐府知名,盖亦当日风气使然。”
因此,李贺诗在体裁上多乐府诗,仅被宋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所收即有46首,这些诗艺术上长于熔铸词采,驰骋想像,运用神话传说,创作鲜明形象。又喜袭用乐府诗题,如《将进酒》《塞下曲》《雁门太守行》《走马引》《大堤曲》《猛虎行》《巫山高》《江南弄》《摩多楼子》《塘上行》《夜坐吟》《上云乐》《艾如张》《上之回》《神弦曲》《莫愁曲》《有所思》《少年乐》等。有时对乐府旧题加以改造,如将《长歌行》《短歌行》并为《长歌续短歌》,《箜篌引》衍为《李凭箜篌引》,《苏小小歌》改为《苏小小墓》,《秦王卷衣》改为《秦王饮酒》,《公无渡河》改为《公无出门》等。
再次,李贺诗歌除向前人学习外,也善于汲取当代人的创作理论与经验。李贺与韩愈的交往最多,关系最密,受其影响也最大。清代管世铭说“昌谷、樊南,退之(韩愈)之属国也”,吴生也说“昌谷诗上继杜韩”(分别见《读雪山房唐诗序例·七古凡例》及《跋李长吉诗评注》)。李贺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受了韩愈诗歌创作的影响:一是吸收韩愈“词必己出”“惟陈言之务去”的理论并付诸实践,形成了好奇背俗,戛戛独创的语言特色;二是因家境贫寒,精神压抑,故对韩愈由胸中磊落不平导致的奇险怪僻的诗风,发散性的思维与跳跃性的艺术结构易于接受;三是受韩愈反对骈偶化,提倡以文为诗的影响,李贺诗歌较少有骈偶句,《乐府诗集》所收46首诗中,有36首没有使用对偶句,其余诗仅用了一联或两联对偶句。另外,李贺诗有句无篇,好苦吟的作风也多少受到了孟郊、贾岛、姚合等人的影响。正因如此,不少人认为李贺属于韩孟诗派中的人物。

△《民国间古代文学研究名著导读》,王友胜、李鸿渊、林彬晖、李跃忠著,岳麓书社2010年出版
三
李贺从前辈诗人那里汲取了丰富的艺术营养,同样的,他对当时及后代诗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李贺生前即诗名卓著,在当时即赢得了众多诗人的喜爱、学习与效仿,其诗一经写成,便被乐工重金购买,谱上乐曲,播于管弦,传唱天下,“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其友人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诗序》中说“贺名溢天下,年二十七,官卒奉常,由是后学争效贺,相与缀裁其字句,以媒取价。”《旧唐书·李贺传》亦谓“其文思体势,如崇岩峭,万仞崛起,当时文人,从而效之,无能仿佛者。”可见当时学长吉体已成为一种时尚,形成了一股“李贺热”,且莫说张碧、刘言史、庄南杰及后来的韦楚老、陈陶等仅有些知名度的诗人要摹拟李贺诗歌,就是著名诗人李商隐、温庭筠、李群玉等写诗也多取法李贺诗风。
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二六说“韦楚老乐府七言有《祖龙行》,正效长吉体也。”吴生《跋李长吉诗评注》说“昌谷诗上继杜韩,下开玉(李商隐)”。朱自清《李贺年谱》亦云李贺乐府上承齐梁宫体,“下为温庭筠、李商隐、李群玉开路”。李商隐的艳情诗《河阳诗》《河内诗二首》《燕台诗四首》哀感玩艳,奇诡波峭,颇受长吉体影响。温庭筠不仅写诗取法李贺,而且其词的风格浓艳,亦近李贺。
李贺奇诡怪诞的诗风也为好奇斗异的宋代诗人所学习效仿,许学夷说“宋人奇变亦自足万家,七言古学长吉而诡幻过之。宋初学李贺者有萧贯、钱易、龚宗元、田锡等,《宋史·萧贯传》甚至说他“词语清丽,人以比重李贺。”他们效仿长吉体,与其诗讲究藻饰和富丽精工有一定关系。北宋中后期及南宋时期,欧阳修《春寒效李长吉体》、秦观《拟李贺》、张耒《福谷怀古》、李纲《读李长吉诗》、徐俯《李贺晚归图》、陆游《艾如张》、周密《拟长吉十二月乐府并闰》等诗刻意效仿、摹拟长吉体的痕迹十分明显。曾巩的《芙蓉台》,何焯说“尖新之句直似李长吉”(何焯《元丰类稿·诗》,《义门读书记》卷四十),苏轼的《武昌铜剑歌》,方东树说“奇妙不减昌谷”《昭昧詹言》卷十二)。宋末谢翱诗受李贺影响尤大,胡应麟说“李长吉,谢皋羽得其遗意”,又说“宋末盛传谢皋羽歌行,虽奇邃精工,备极人力,大概李长吉锦囊中物耳。(《诗薮》外编卷六)虽是从一正一反两方面说的,但大抵道出了谢翱与李贺诗歌的渊源关系。
李贺诗“调婉而词艳”,与词善言情,风格软媚香艳相接近,故其对宋代词人影响亦大。最先阐述李贺诗与宋词关系的是明代的许学夷,其《诗渊辩体》卷二六云“李贺乐府七言,声调婉媚,亦诗余之渐。”李嘉言先生在《词的起源与唐代政治》中说:“纵令李贺不懂得音律,只凭他那‘怨郁凄艳之巧’,亦足可与词结为总角之交。”袁行霈先生也说“李贺虽然没有填过词,但他的诗却是由诗过渡到词的一座桥梁。”李贺诗对宋代贺铸、史达祖、吴文英词的影响尤大,姜夔《梅溪词序》说史达祖词“奇秀清逸,有李长吉之韵”(黄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引),张炎《词源》卷下也说“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练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金代诗坛赵秉文、李天英、王飞伯、刘龙山等人对李贺诗也心追力摹,赵氏有《拟李长吉击毯行》诗,其《呈保定诸公》还自豪地说时人“呼我刘昌谷”。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七引),张炎《词源》卷下也说“贺方回、吴梦窗皆善于练字面,多于温庭筠、李长吉诗中来。”金代诗坛赵秉文、李天英、王飞伯、刘龙山等人对李贺诗也心追力摹,赵氏有《拟李长吉击毯行》诗,其《呈保定诸公》还自豪地说时人“呼我刘昌谷”。
元代诗坛,尊唐黜宋,学习李贺的也不少,元初诗人郝经《长歌哀李长吉》、刘因《李贺醉吟图》、马祖常《上京效李长吉》等效仿于前;元代中期于石《续金铜仙人辞汉歌》、刘诜《天上谣·戏效李长吉》、吴景奎《拟李长吉十二月乐辞》、郭翼《和李长吉马诗九首》等步武于后(分别见顾嗣立编《元诗选》之《紫岩集》《桂隐集》《药房樵唱》《林外野言》);到了元末,诗坛甚至出现了一个“李贺时代”,胡应麟说:“元末诗人,竞师长吉”(《诗薮》内编卷三)。学李贺者中有张宪、李序、陈樵、李裕、项炯等,其中以杨维桢最为杰出。他分析了历来效仿李贺诗的两种倾向:“故袭贺者袭势,不袭其词也。袭势者,虽蹴贺可也;袭词者,其去贺日远矣,今诗人袭贺者多矣,类袭词耳。”(杨维桢《大数谣》吴复注引)杨氏本人效李贺的诗则颇“有李贺之奇诡”,其《鸿门会》诗效仿李贺《公莫舞歌》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学生吴复称扬其“酒酣时常自歌是诗,此诗本用贺体而气则过之。”
明清时期,学李贺者不乏其人。徐渭不仅大量批点李贺诗,创作上也刻意学之。陈式《重刻昌谷集注序》说:“今《文长集》中,五七言古亦有学之而得其似者”,贺贻孙《诗筏》中说:“徐文长七言古,有李贺遗风”,清代黄景仁、龚自珍、黄遵宪等人也借镜或学习李贺诗。英年早逝的黄景仁诗多写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穷困潦倒、
 傺失志的处境,情调感伤,充满磊落不平之气,与李贺可谓隔代知音;龚自珍诗歌的艺术风格虽主要渊源于庄子与李白,但其“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前,欲捉已逝”(程金凤《己亥杂诗书后》)的浪漫诗风,也受到李贺的一些影响;黄遵宪诗歌创作取法于《楚辞》与汉魏乐府,艺术结构善于变化,开合动荡、摇曳多姿等方面亦与李贺诗风近似。蒲松龄《聊斋志异》写幽冥世界以寄其忧愤,“使花妖狐魅,多见人情,和异可亲,忘为异类。”多取法于李贺的神鬼诗;曹雪芹《红楼梦》中诗词凄婉感伤的格调,也可以从李贺的闺怨、宫怨诗中找到渊源。
傺失志的处境,情调感伤,充满磊落不平之气,与李贺可谓隔代知音;龚自珍诗歌的艺术风格虽主要渊源于庄子与李白,但其“变化从心,倏忽万匠,光景在前,欲捉已逝”(程金凤《己亥杂诗书后》)的浪漫诗风,也受到李贺的一些影响;黄遵宪诗歌创作取法于《楚辞》与汉魏乐府,艺术结构善于变化,开合动荡、摇曳多姿等方面亦与李贺诗风近似。蒲松龄《聊斋志异》写幽冥世界以寄其忧愤,“使花妖狐魅,多见人情,和异可亲,忘为异类。”多取法于李贺的神鬼诗;曹雪芹《红楼梦》中诗词凄婉感伤的格调,也可以从李贺的闺怨、宫怨诗中找到渊源。

△《纳兰词注》,王友胜、童向飞注,岳麓书社2005年出版

现代诗人中,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的诗颇受李贺意识流创作的影响。毛泽东也颇喜爱读李贺的诗,他在诗词创作中常化用李贺诗成句,如“一唱雄鸡天下白”(《浣溪沙》),出自李贺《致酒行》“雄鸡一声天下白”;“人生易老天难老”(《采桑子·重阳》),出自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红雨随心翻作浪”(《送瘟神》其二),出自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红如雨”等。
古代学李贺者代不乏人,法乳不断,虽间有佳作,然从整体上说,或追和原诗,或摹拟诗题,或袭其字句,而鲜有真正得其神韵者。没有李贺的亲身经历与病态体质,没有他耽于幻想、偏于主观的怪僻心理,是很难学像长吉诗风的。清代陈式《重刻昌谷集注序》说:“昌谷之诗,唐无此诗,而前乎唐与后乎唐亦无此诗。”此成为的评。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曾国藩为什么要编选这部古文选本?
慈禧是如何整顿恭亲王奕,正式独掌大权的?
楚辞为什么那么美?
世人皆醉,斯人独醒:郭嵩焘独醒的勇气与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