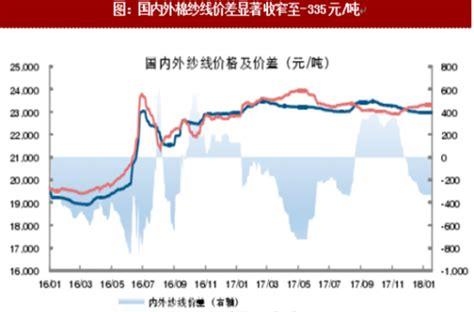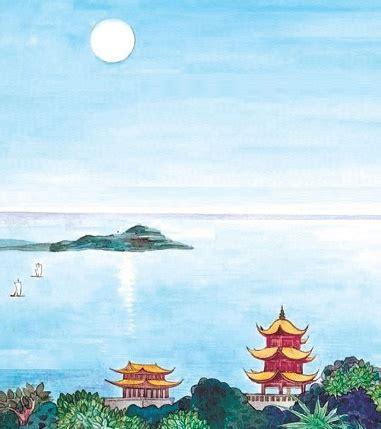现在听李宗盛的歌是一种什么样的人生体验?
“我终于失去了你,在拥挤的人群中”。
那种辉煌、惘然中失落的感觉,重锤击心的感觉。

我第一次有概念“李宗盛的歌”,是杨佩佩工作室电视剧《碧海情天》那剧,刘松仁、李立群和叶童演的。主题曲《凡人歌》。
我一听就觉得很奇怪。那时我还小,只觉得歌词真是负能量。什么叫“多少同林鸟,已成了分飞燕。”什么叫“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偏这家伙——众所周知——唱歌还吊儿郎当的,半念半唱,“已成了分飞燕”,最后三个字还下重音,你是指望成了分飞燕是怎么着?

那时我还小,还不觉得李宗盛的嗓子好听。
他唱歌有种大胡茬子味,就像刮完了又长了两天的胡茬子,挂手,蹭人,颗颗粒粒的。那会儿我的审美,还停留在老辈们播的李谷一和邓丽君:瓷器般圆润流转,羚羊挂角的声音里。
还是杨佩佩工作室的电视剧。《末代皇孙》。我是冲着周海媚去的。这里插一句,周海媚真是娇媚妖娆又楚楚可怜,说句高圆圆粉丝不爱听的话,只论周芷若,高圆圆拼命学都没学到周海媚的味道。
《末代皇孙》的片头曲,是《鬼迷心窍》。开头就李宗盛式的大沉重,“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连着几句都是下行音符,听不惯。但中间,忽然就扬了起来:
“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
这份痴劲,忽然就击中我了。

当然那时我还小,还不明白这些词句的意味,不明白他最后为什么要苍凉地“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后来就知道了,《我是一只小小鸟》,是他写的;《领悟》,是他写的;《爱的代价》,是他写的。后来,《阴天》,后来,许茹芸的《真爱无敌》(空城计?)。我自己也慢慢长起来了。
中学时偷偷喜欢过的、比我大一岁高两届的女孩子,去上大学了。憋着的难过感,听张艾嘉“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听很久,一口气,呼出去了。
在大学里,自己租了房子一个人住,晚上一个人写稿,抬头看窗外灯火阑珊时,“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小鸟飞呀飞,却怎么也飞不高。”把背仰上椅子,叹一口气。
现在想,许多时候,不是李宗盛多完美符合我的心境,只是年纪渐长,会慢慢地明白他那些词与歌,一鳞半爪地。然后,会自然地往那边靠。对喜欢“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少年们而言,李宗盛是个很好的对象。“对啊,他说出了我们的心声!”哪怕没有那么多“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的感觉,也会捧着《阴天》,听。

再后来,经历的事情多了,真有点明白李宗盛了——不只是代入感的情境。
李宗盛很通透,并不高唱颂歌,傻白甜,“多少同林鸟,已成了分飞燕,人生何其短,何必苦苦恋”。他挺明白的。
但他也并不遗世独立。他唱男人女人。他知道人事无常,但他挺入世,而且以身作则地享受这点甜与苦中的诗意。
怎么说呢?他那胡渣子般的嗓音,小时候听,颗颗粒粒,长大后听,像黑巧克力,像雪茄,甜味不多,主要是苦与酸,以及,厚实。
小孩子时爱吃甜的,长大后,才能懂得品味苦。
李宗盛不劝你超脱,只是拿着颗颗粒粒的嗓音,半念半唱,自我解嘲似的,说段子。最代表这种态度的,是《最近比较烦》。动听悦耳的小旋律,自我解嘲的小段子。玩儿呗。
我有时候,会想起《鹿鼎记》里的美刀王胡逸之。看着乡巴佬一般的小老头儿,其实身负绝代武功,却又偏偏对陈圆圆一片痴情,老来犹且如此。他的痴劲儿,到了这般地步:竟能记住这种细节:
“这二十三年之中,跟她也只说过三十九句话。她倒向我说过五十五句。”
吴六奇试图劝他时,胡逸之如是说:
“吴兄,人各有志。兄弟是个大傻瓜,你如瞧不起我,咱们就此别过。”
这种自知痴得过分,却并不跳出来的劲头,下面这句话里,感慨系之:
“不知疲倦地翻越每个山丘
……
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
每次听到这句歌词,我老想到《东邪西毒》里张国荣那句话。“以前看见山,就想知道山的后面是什么。现在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小时候,总觉得“过了一个节点,一切都好了”。读书时,相信上了大学一切都好了。上大学时写东西,觉得自己出版第一本书后一切都好了。来法国前,相信过了这一关就什么烦恼都没了。
然而并非如此。世上并没有一个“你过去了,从此无烦忧”的山丘。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不消多提。时间流逝最让人难过的真相是,年少时总还以为,过了这座山就没事了,再怎么烦恼,心里有个念想,颇有点“做完这一票,就回老家结婚,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之意;但多少次撩撩绕绕之后,才多少明白并没有结束的那一天——断了念想的翻山越岭,才是真的疲惫。
但这个事实多残忍啊。李宗盛还是唱出来了。就像他二十年前问:“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而在二十年后,他看似嬉皮笑脸地,把自己的演唱会命名为《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做个大叔好》这么一个冗长的名字,再唱一首《凡人歌》。这调子,就像胡逸之爱了陈圆圆二十三年后,对吴六奇那句自嘲:“兄弟是个大傻瓜。”
是自嘲,然而并不后悔。
他看破也点破了,用他颗颗粒粒的,粗黑巧克力似的嗓子。但他没走远,还是坐在人堆里,跟我们一起,用他坑坑唧唧,半念半唱的调子,抒情一下子,又沉郁一下子。
我们很多时候,怕的其实不是失败,而是被遗弃。
李宗盛一直没忘记我们。他看通透了,但还在尘世间,与我们这些寻常男女同甘共苦。同甘不难,主要是,共苦呢。